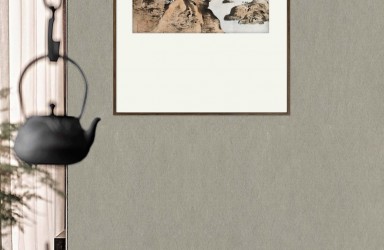瞿谷量,上海嘉定人,美籍华人画家, 1936年3月生于上海嘉定,擅长绘水粉水彩画,钟爱安徽黄山,曾十七次上黄山写生。 瞿谷量其作品笔下的黄山,清新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,其色、其笔、其气、其神均与他人明显不同,表现出黄山的神韵,和中国画的笔墨功底。
人物基本信息
自幼喜爱绘画,曾随陈秋草习画,打下深厚的西洋绘画根基。
1954年 进新中国美术研究所(原白鹅画会),随从陈秋草先生学画。
1956年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。
1957年 作品入选“上海青年画展”,水彩画《上海人民公园早晨》获鼓励奖。
首上黄山写生,与画家谢之光先生同行,作水彩画《蓬莱三岛》等,在散花精舍巧遇云海蜃楼奇景。
1959年 三幅作品入选全国水彩画展,于北京美术馆展出,署名瞿昉。《上海人民公园雪景》选送“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”,于苏联莫斯科展出。
1960年 下放劳动于青浦饲养场。
1961年 《蓬莱三岛》、《上海南京路》、《上海人民公园雪景》入选《水彩画范本》,由北京朝花出版社出版。
个人简介
旅美画家。
19岁时随曾创办白鹅画会的陈秋草习画,打下了西洋绘画的基础,
1956年进入上海人美社工作并从事水彩画创作。次年,谷量第一次登上黄山,创作水彩画《黄山蓬莱三岛》。
1974年,瞿谷量作为上海美校的教师带学生二上黄山。
1982年瞿谷量移居美国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身处异域的他,愈发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伟大和深厚,需要作深入的学习和研究。
同时,他对黄山的眷恋之情也愈发地梦萦魂绕。
到了上世纪90年代,瞿谷量几乎是每年都要从纽约飞到黄山,这才是瞿谷量与黄山情缘真正的开始。瞿谷量画黄山,是画家艺术审美和艺术表现的需要,也是画家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需要。正如他所说,黄山的中国味特别浓。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登上黄山,至今已达十四五次之多。 瞿谷量登黄山、画黄山,不是简单的重复,而是有意识地赏黄山四季之景、写黄山四季之美。他笔下的黄山,清新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,其色、其笔、其气、其神均与他人明显不同,表现出黄山的神韵,和中国画的笔墨功底。
个人著作
《瞿谷量画集》,中国画的传统,明代的董其昌曾一分为二,一路以明清文人画为代表,注重“以画为乐”,即作为翰墨的游戏,所讲究的是“画外功夫”,即以人品、诗文、书法的修养置于“画之本法”之上,以主观置于客观之上,笔墨置于形象之上,“以形象之丰富论,画不如生活,以笔墨之精妙论,生活决不如画”。
所以,在较少数“吾曹”、“至人”,可以“一超直入如来地”。
另一路以唐宋画家画(包括画工画和文人正规画)为代表,注重“身为物役”,即作为艰苦的劳役,所讲究的是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“画之本法”,以造型技术置于“画外功夫”的修养之上,以客观至于主观之上,以形象置于笔墨之上,“以形象之丰富论,画高于生活,以笔墨之精妙论,生活决不如画”。
所以无论是极少数的“吾曹”、“至人”,还是大多数的普通画家如王希孟、张择端,都可以“积劫方成菩萨”。 长期以来,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,认为前者是传统中表现的、先进的、创新的、高雅的、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,后者只是传统中再现的、落后的、保守的、俗气的、贵族性封建性的糟粕,却忽视了前者只适用于具备了特殊条件的“吾曹”、“至人”,而后者却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画家。画坛的风气,撇开否定传统的不论,凡赞同继承弘扬传统的,几乎都把前者看作是捷径,争而趋之,而把后者看作是歧途,避之不及。
这种情况,有些像钱锺书先生在《诗可以怨》中所分析,虽然艺术创作的动力可以是快乐,也可以是痛苦,但由于人们普遍认为“穷苦之言易好,欢愉之辞难工”,所以,即使没有痛苦经历的诗人,也更愿意“不病而呻”。
这里面包含一个希望:有那么便宜和侥幸的事,不是“穷苦”的诗人,只要模仿“穷苦”的言词,也可以成为好诗;不是“吾曹”、“至人”,只是模仿“吾曹”、“至人”的“无法而法”,同样可以成为“至法”的好画。
作品评价
对于画家来说,由于他们比之诗人更缺少文化的修养,自然也就更缺少自知之明,所以,很少有不认为自己是天才的。既然自己是天才,自然也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走“至人”成大才的捷径,而不应该走常人成小才的艰难之道。
过去,陆俨少先生说过“老实画”和“聪明画”的问题,大体上正是对应了这两种不同的传统观。瞿谷量对于传统的取法,一度也是作如此这般的选择。然而,经由他和谢稚柳、陈佩秋、刘旦宅等先生的长期交游,他很快醒悟到自己不是“至人”天才,即使自己真是“至人”天才,至少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“至人”天才。既然自己不是“至人”“天才”,或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“至人”“天才”,那么,天才的成才捷径自然也就不适合自己。适合自己的,只能是“积劫方成菩萨”的常人成才之道。 有了这样的自我定位,他便自觉地从“无法而法”、“我用我法”的捷径上退了回来,老老实实地在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“画之本法”上一步一个脚印地修炼。他把黄山作为自己艺术攻坚的主要对象,几十年来,调动各种技术、手段为黄山作写生,取得了对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、笔墨与形象的全新认识,实际上也正是传统的、古典的认识。
有一种观点认为,艺术真实为了拉开与生活真实的距离,必须“舍形求神”,轻视对于对象的实的方面的深刻把握,而注重对于对象的虚的方面的体悟,否则的话,就会论于生活真实的翻版,就是“与照相机争功”。诚然,像石涛、黄宾虹那样,“舍形求神”的生活体验方法,“目击而道存”,“不见骊黄牡牝”、“不似之似似之”,自不失为一种艺术形象的塑造方法,但是,以此作为唯一的方法并借此否认“以形写神”的方法,却未必可取。
瞿谷量作品
因为一,石涛等的方法,对于“至人”、天才自然是合适的,对于大多数普通的画家,“舍形”好办,但舍了形却未必都能达到传神,结果“舍形求神”、“不似之似”往往成了画家们“舍形”、“不似”的借口,却不顾了“求神”、“似之”。
第二,李成、范宽、郭熙等的“以形写神”、“形神兼备”,未必就是必须摈弃的“与照相机争功”的艺术形象塑造方法,而恰恰正是这一方法,不仅适合于李成等大师,同时也是适合于王希孟、画院的众画师等最大多数普通画家的。
由于瞿谷量把自己定位在普通画家而不是天才的位置上,所以,他对黄山的观察体验巨细无遗,无微不至,尽可能地达到深刻、全面,并在此基础上由形及神,加以提炼、概括,形成为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形象。我们看他笔下的苍松、怪石、烟云,不是黄山生活真实的翻版,却正是黄山艺术真实的提炼,而绝不会把它们与其他什么名山的风景混淆起来。
事实上,由于任何“外师造化”都是“中得”于画家主观的“心源”的,所以,以主观置于客观之上的“舍形求神”固然可以拉开与生活真实的距离,以客观置于主观之上的“以形写神”同样必然拉开与生活真实的距离。宋人的艺术实践证明了这一点,瞿谷量的艺术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关于笔墨与形象,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是笔墨作为中国画的本质,而形象则是为笔墨的抒写服务的,中国画的“气韵生动”,归根到底就是笔墨的精妙,如同样的披麻皴、解索皴,同样的个字、介字、在不同画家的创作中表现为不同水平的笔墨效果,而这样的形象,往往也不再被称做“形象”而是被称做“笔墨程式”。
然而,这一认识,同样只适合于董其昌、石涛等天才的画家,而不能适合于最大多数的普通画家。即以明清画史而论,有多多少少的画家追随了董其昌、石涛的画风,小四王、后四王、扬州画派乃至“风漫中国”的逸笔草草,结果,抛弃了形象的刻画,“一超直入”的笔墨的抒写效果却并不理想,傅抱石先生甚至斥为“荒谬绝伦”!
与这一观点相对的,是唐宋的画家都把形象作为创作的核心,笔墨则是为形象的塑造服务的,配合了形象的千变万化,笔墨也应该千变万化,当用精妙的笔墨刻画出了“形神兼备”的艺术形象,一幅作品才称得上是“气韵生动”。遵循了这一观点,所谓“纲(形象)举目(笔墨)张”,李成等少数天才的大师也好,王希孟等最大多数的普通画家也好,通过“积劫”,无不成就了各自的“菩萨”果。
由于把自己定位在普通画家而不是天才的位置上,所以,瞿谷量对于形象与笔墨关系的认识,完全是追随了宋人的传统,他决不是从“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”来经营创作的笔墨效果,而始终是根据黄山艺术真实的形象塑造需要,量体裁衣地来运用勾、皴、点、刷、渲染等笔墨的技法。与宋人的山水一样,观赏他的作品,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黄山的形象,千岩万壑,苍松怪石,隐现于灭没变幻的烟云岚光之中;深入地玩味,才能感受到这样的形象,乃是运用了轻重疾徐、粗细转折、疏密聚散、枯湿浓淡的不同笔墨刻画而成。